苔丝送走妹妹艾米莉,快刀斩乱麻,摆平、了清了毒豆腐事情,回到家,已经是晚上十二点钟了。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,以示与之前的不愉快具备拜拜。要不是妹妹正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,广济公司就已经不存正在了,灰飞烟灭。半个多月以后,苔丝的精神不停高度紧张,神经紧绷,基础就没吃过一顿好饭,睡过一个安生觉。怪的是:连平时不停很准的月事,也足足推迟了三四天,量也多了。而自己还偶有失眠、盗汗、惊厥、胸闷、气喘等特殊现象。苔丝从碗橱里找出一碗冷饭,用开水泡了泡,就着一碟咸萝卜条,狼吞虎咽地填饱了肚子。然后,她脸也不擦,脚也不洗,用被子蒙住头,倒头便睡。无债一身轻,她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紧张过了,讨帐人围追切断,不停吵得她无法宁静。正在梦中,苔丝又看见了仙童。他一点都没变,还是阿谁老样子。个子颀高,皮肤白皙,眼睛很长、很细,瞳仁闪闪发光,呈四十五度角微微向上翘起,是传奇中的那种丹凤眼,很迷人,特魅惑;笑起来,他的脸上有两个甜甜的酒涡。一时里,苔丝不知不觉地看呆了。纵然现场很冷落,也很安谧,客人们衣冠楚楚,熙熙攘攘。可苔丝还是正在人堆里,一眼就认出了他。多年的两小无猜和耳鬓厮磨,让苔丝已经民俗了仙童身上的那种气味。哪怕就是蒙上眼睛,她也能准确地把他从人堆里揪出来,从来就没失过手,可以说是百试不爽。而仙童却左拥右抱,倚红偎翠,被一帮女孩子们环绕着,他举着喷鼻槟,高谈阔论,道不完的纸醉金迷,说不尽的风流倜傥。女孩子们也很积极,对着仙童撒娇,放电。仙童不是柳下惠,可以坐怀稳定。他开始也是个汉子,一个有正常生理需求的汉子。他的脸莫明其妙地红了,眼睛却特地凌厉,盯住女人优美的面庞,想入非非,看个一直。刚先导,苔丝感到自己看错了,看花了眼,可她擦亮了眼睛望了往时,泡正在女人堆里的,倚红偎翠的,确切实实就是仙童。天啦!自己洁身自好,守身如玉,甚至不惜割腕自尽、以表忠贞的汉子,原来、原来是个道貌岸然的伪正人,竟然这么快就具备地倒戈了她。什么卿卿我我?什么海誓山盟?都是他妈骗人的鬼话。苔丝表情苍白,心灰意冷,她低着头,款款地走了往时,端起桌子上的一杯喷鼻槟,出其不意,兜头盖脸地朝仙童泼了往时。莺莺燕燕们就像大白天见了鬼,大声尖叫,四散而逃。仙童猝不及防,一下子被喷鼻槟泼醒,正要发作。他一看是苔丝,愣怔了一下,匆忙摔开环绕着的女孩子们,步子蹒跚地追了出去,一边追,一边狂喊:“苔丝,你等等我,等等我呀!”空气紧张得就要爆炸,全体都目瞪口呆,仙童悲壮的声音正在乾坤间绵绵无间,久久回响。苔丝一边跑,一边哭,一边大声咒诅。这人,这场景,太让人抓狂,太让人灰心。这还是阿谁让她深爱着的仙童吗?岂非他们之间的爱就这么结束?就这么不堪一击?这么多的日子,她逃婚,流浪,忍饥受饿,担惊受怕,白手起家,苦苦等来的,岂非就是这么一个终局?就是无休无上的倒戈?近了,近了,仙童的脚步声越来越近,且铿锵有力。苔丝甚至还可以认识地听到,他短促的喘息。她想象着仙童追得气喘如牛、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,忍不住想笑。可是该发生的,都早已发生了,雾非雾,花非花,任何都己回不到从前。“苔丝,我的个祖宗,你别跑了行吗?你再跑,就成电影里的套路了!”仙童合拢大嘴呼吸,脸因缺氧而憋得通红。他喘定了一口气,接着又说:“苔丝,你停一停,听我说明一下!哪怕我是个逝世刑犯,是不是也有申诉的权限?法官大人!”苔丝忍俊不住扑哧一笑,脚步也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。她凝住脸,叉着腰,严辞厉色地说:“说,你为什么要倒戈我?跟此外女人们勾勾通搭?你对得起我吗?你的本心叫狗给吃了?我为什么就看上了你这么个陈世美?”“苔丝,我对天起誓,我真的没有倒戈你。溺水三千,我只取一瓢饮。怪只怪今日是王母娘娘寿诞,我多喝了一杯酒,才让美女们钻了空子,才让你抓了个现行。我起誓,我保证,下次再也不敢了,下次特定对你绝对忠诚。”“那钻空子的美女都是谁?也不给我介绍介绍?”苔丝心如电转,一脸的恶作剧。“这…这…”仙童有些踌躇,支吾了一阵子,他接着又说:“苔丝,我就干脆来个竹筒倒豆子—质朴交代。穿红的阿谁嘛,叫毛青鸾,是王母娘娘的座下侍女,我仙童的救命恩人。满头珠翠的阿谁,叫盖铃铃,是王母娘娘的贴身侍卫,功夫不错,咱们时常正在一起切磋。”“切磋什么?切磋见不得人的功夫吧?”苔丝语带讥诮。“苔丝,我冤枉,我是那样的人吗?本公子不停守身如玉?”仙童张口结舌,大声申辩。“你冤枉?鬼才信?刚才,你为什么要那样?质朴交代,坦白从宽,抗拒从严,这下哑口了呗!”苔丝得理不饶人,有些暗自豪意。“法官大人,冤枉哪冤枉,刚才,我看见一只蚊子,歇正在毛青鸾裸露的大腿上,帮她拍打了一下,引起了你的误会,天啦,岂非这也有错?”“天庭里也有蚊子?你这是籍词?你这是骗鬼?”“法官大人,你真是罕见多怪!天庭里不仅有蚊子,而且又大又多。不信,你睁开眼睛看看。”苔丝不信,抬起首,朝天上望去,只见几只蚊子嗡嗡地飞了过来。而且其中的一只,不偏不倚地落正在苔丝的脸上,似乎要证明些什么?伸出探针,就要吸血。仙童往前一步,手重轻一抄,就把蚊子活活地捏正在掌心,像一个刚缴获的战利品。顷刻间,苔丝的脸红得像涂了一层胭脂,娇俏得如同天边的晚霞。仙童像受了鼓励,或有了某种默许,卑下头,全神灌输,吻向苔丝性感、红润的嘴唇。苔丝也疯狂地回吻着他,就像被魔鬼之手一下子拨动了情欲之弦。甜蜜来得太忽然了,让苔丝有些措手不及。她就像一只趴正在花蕊上吸食花蜜的工蜂,或一只吊正在藤架上的倭瓜,紧紧地搂住仙童的脖子,正在他的脸上吻个一直。无论是时长,还是密度,都已经冲破了新的吉尼斯世界记录。不知过了多久,仙童抬起首,喘定了一口气,泪光闪闪地笑着说:“苔丝,你又瘦了。不过,你还蛮利害,一次性可以深潜这么长,这么久,破了吉尼斯世界记录。”“你坏,你坏!来天庭才多久,你就学坏油嘴滑舌了,哼,讨厌!”苔丝伸出一根指头,正在仙童的额头上戳了戳。嘿嘿,仙童有些傻乐,顺势抓住了苔丝的手,顺势一扯,顺势把她拥入怀中,附住她的耳朵,絮絮地说:“苔丝,忘了告诉你了,你还有二劫。一劫是三天之后的暴风雨之夜,天雷会劈开你屋前的木樨树,压垮你栖身的房屋;另一劫是你会遭受坏人的抨击,有血光之灾,能不能躲过一劫,就看你的造化了。切记,切记!”苔丝是喊着仙童的名字,从梦中哭醒的。一醒悟来,已经这天上三竿,旭日临窗。苔丝擦了擦脸上潸然的泪水,一个骨碌从床上坐了起来,梦中的任何彷佛还历历正在目,言犹正在耳。怪了,她怎么会梦见天庭?梦见仙童呢?岂非是上天眷顾?怜惜?总之,能够见到仙童,她已经很知足,很幸福了,哪怕是正在虚无缥缈的梦中!因为有梦,所以苔丝非常欢畅。她是吹着口哨起床的,又正在口哨声中刷牙,洗脸,梳头,妆扮,正在镜子里左顾右盼,把自己收拾得漂优美亮。然后,她又正在口哨声中,步子轻快,神采奕奕地走进了广济公司,阳光帅气,暮气强壮的样子。公司里的人都发现,苔丝像换了一限度似的,她变得话多了,爱笑了,宽厚妩媚,荣耀照人。她时常莫明其妙地脸红,莫明其妙地发呆,莫明其妙地偷偷傻笑。爱情的力量真是太伟大,它可以颠覆全部,改革任何,让不可能变成可能。不知是故意,还是无意。天天上、上班,每次正在屋前的那棵大树下路过,苔丝都要正在树干上摸一摸,拍一拍,发一阵子呆,举头凝视长久,不由自主地想起仙童正在梦里的嘱咐。她怎么也不敢笃信,这么一棵好生生的大树,会正在三天之后,会被雷电劈开,烧焦,付之一炬。苔丝对大树也有一些研究。这是一棵枝繁叶茂、高宏壮大的木樨树,桂花科,双子叶类,常绿阔叶乔木,水桶般粗细,开一树黄灿灿的繁花,别名岩佳、金粟、汉桂。岂非树也跟人一样,也有凹凸?也有宿命?也得接纳命运的讽刺和摆布?也逃不脱丛林规则?不管苔丝信不信,灾难还是发生了。仙童果真料事如神。三天之后,西津县真的下了一场暴雨。风很大,震耳欲聋的霹雳一次次地正在半空中炸响,地球像一只懦弱不堪的蛋壳,正在巨震中一直地晃荡。雨,瓢泼般的大雨,就像天河一下子溃决了,挟杂着雷霆之势滚滚而来,如同钱塘江的怒潮。最骇人的还是闪电,蓝幽幽的,如同千万条火蛇正在天空中蜿蜒。梦乡似的,正在一片时里照亮了天空,又正在一片时里寂灭。雨,鞭子似地抽打着窗棂,整个屋宇似乎都正在震颤。苔丝又惊又怕,拥着被子坐了起来,战战兢兢,蜷成一团,像一只待宰的穿山甲。猛地,轰隆隆一声巨响,一道火光从天而降。空气中,弥满了工具烧糊、烧焦了的怪味。紧接着,喀嚓一声,屋前的木樨树一东一西,分红了两半,东边的一半扑通一声砸正在屋檐上,如一记重锤,檀木折断,瓦片飞溅,墙壁垮塌。外部反应催生了内部转移。天雷劈开屋前的木樨树,木樨树压垮房屋,垮塌的墙壁又寂然一声倒下来,砸坏了苔丝寝息的床铺。任何就像多米诺的骨牌,一环套着一环,一起接着一起,滴水不漏,环环相扣,命运太悬,基础没有预留让人应对、喘息的机会。好险哪!苔丝紧紧地捂住了自己的耳朵,喘成一团,抖成一堆,就像一只美国火鸡,把头埋正在沙堆里,顾头不顾尾。有了仙童梦中的嘱咐,苔丝半信半疑,抱着试试看的心境,暗暗地把床往后移了一尺。也就是这小小的一尺,床靠柜子更近了,柜子高,坚实,与床之间酿成了一个逝世角。苔丝就躲正在这个逝世角里,逢凶化吉,又逃过了一劫。风还正在下,风刮得更起劲了。苔丝困正在废墟里,拥有了屋顶的樊篱,雨水混着汗水,搀杂着泪水沁进嘴里,风味又腥又涩。苔丝活动了一下四肢,身体无甚大碍,只要脸、肘、大腿等处剐破点了皮,压根就逝世不了,危及不到生命。苔丝咬紧牙关,鼓足勇气,想自己爬出去。可她的头被屋檩和瓦片挡着,肩又靠着一段断墙,身子稍一挪动,手稍一使劲,砖头瓦块就往下掉,屋檩子也嚯嚯地响个一直。自己既使不被断墙砸逝世,也会被檩子和瓦片活埋。动不了,苔丝就只能等,等人来拯救,等奇怪发生。不大片时儿,雨小了一点,风也有所收敛。隐隐的雷声里,有人大喊:“二毛,快来看啦!苔丝老总屋前的木樨树被雷劈开了,还烧逝世了一条大蜈蚣。天啦,谁见过这么大的蜈蚣?”喊的人叫大毛,苔丝闲熟,他还是广济公司属下一家豆腐工厂的工人。紧接着,二毛也打着伞出来了,他不仅发现了被闪电烧逝世的蜈蚣,还发现了苔丝家被大树压垮、压塌了的房屋,可着嗓子大喊:“大毛,不得了,不得了!总司理家的房子垮了,苔丝已埋正在断墙下面。全体快来,救命哪救命!”二毛的声音平缓,尖锐,分了岔,长出了倒须,正在暴风夜里嗡嗡传响,就像锐器划响了玻璃。因而乎,左邻右舍,远处街坊,迎风冒雨,倾巢而出。他们扛的扛锄,拿的拿锹,人多力量大,一眨眼的功夫,就抬走了被雷劈断了的木樨树,移走了檁木,把废墟上的砖头瓦块搬得干索性净。全体喊的喊,哭的哭,叫的叫,打着灯笼火把,终归正在大柜和木床之间,找到了奄奄一息的苔丝。苔丝并没有逝世,她是又惊又吓,心力交瘁,体力重要透支,片刻休克而己。可街坊、邻人们不清晰,一个个都愁云惨雾,失声痛哭起来,如丧考妣,声震云天。
本文地址:http://uas4.7oke.cn/dc/13028.html
版权声明:本内容部分来源于网络,感谢原作者辛苦的创作,转载如涉及版权等问题,请与我们联系处理!
版权声明:本内容部分来源于网络,感谢原作者辛苦的创作,转载如涉及版权等问题,请与我们联系处理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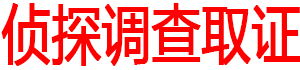

发表评论